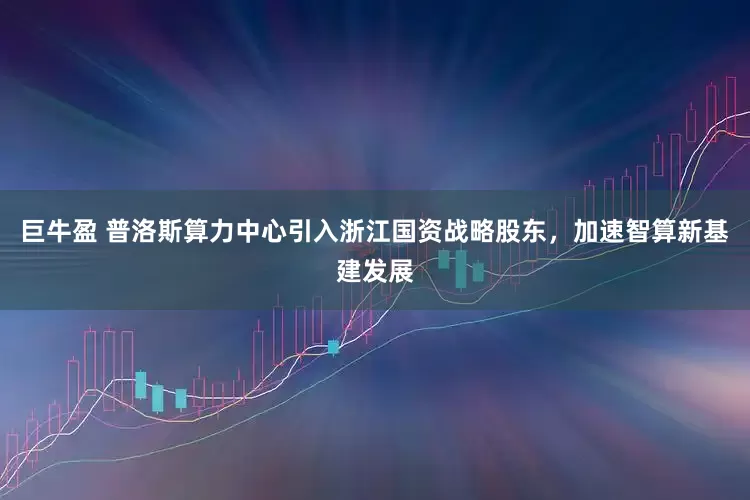上上策 刘伯承去休假,身后跟着两个人,刘伯承笑称:他们是找我要账的

“1953年8月5日清晨,江风直往袖口里钻——’院长,真不带家眷,只带这俩?’警卫员忍不住小声嘀咕。”码头上人来人往,刘伯承微微一笑,看了看身后那位俄文翻译和那位院刊编辑上上策,“他们是来向我讨债的。”一句玩笑,让围观者更加摸不着头脑:休假带翻译和编辑,图啥?

渡船发动,汽笛拉长,惯性把话题抛向了背后。同行者悄悄翻出厚厚资料夹,里面夹着《苏联红军野战条令》原文以及军训部分送审译稿。事情渐渐清晰:刘伯承要在大连“一边疗养,一边清账”,把这部二十多万字的条令重新核校。

假期为何演变成加班?得从两年前说起。1951年春,南京北极阁那幢古色小楼灯火通明,天刚擦亮,刘伯承便在阳台做简短拉伸,随后抓起放大镜钻进书堆。俄文教材、德国战史、苏军战役笔记铺得到处都是。十点左右,他下山进院工作;夜幕落下,楼里依旧沙沙作响。一次老旧电线冒烟,他竟全无所觉,警卫硬是把他拽到院子才避免火情,旁人看得心惊。
高强度劳作很快在身体上留下痕迹。刘伯承右眼在战争年代就已失明,全部视力寄托在左眼。长时间盯纸,视神经胀痛,头晕、失眠随之而来。偏偏那一年上上策,军事学院高级速成系急需一堂“集团军进攻战役”课程,他顶着巨压亲自备课——37000字提纲,18天内完成,从黑墨修到蓝墨,再到红墨定稿,整张纸像战场标图,密密麻麻。六小时授课结束,学员直呼“过瘾”,教员感叹“老院长下手太狠”。可当晚刘伯承就因头痛到窗前吹冷风,连水杯都端不稳,这件事一直没对外声张。

身体发出的警报越来越急。中央三番五次让他外出疗养,他总说“忙完这件就走”。1953年暑期学员放假,学院事务稍松,他才松口:到大连歇两月。然而,翻译室同志把条令校译稿连夜送来,他看完眉头一皱,不少术语对不上实战,用词模糊。于是临行前拍板——翻译、编辑跟着走,统统在海边“还账”。
列车过山海关,海面折射着晃眼日光。下榻处紧靠海滩,本是疗养圣地,可刘伯承第二天就改成“翻译室”。早六点出门呼吸海风,六点半进屋对照原文。瓶装眼药水、放大镜、红蓝黑三支笔和一本词典摆成了“作战编组”。哪一句俄文含混,他先查资料,再让翻译大声朗读,随后和编辑琢磨中文表达。午饭十分钟解决,下午继续校对。夜深人静,他披衣到助手房里复盘,房门虚掩,海浪声伴着讨论声此起彼伏。

一句“每个字都压着一个兵的命”不是修辞,而是底线。他认为军事著作翻译离不开三项硬本领:外文、中文、军事学识。缺一,行文就会走样。比如“集中突击”这一条,他前后斟酌五次,既要契合苏军惯用术语,又得贴合中国军队指挥习惯。遇到苏军坦克、炮兵协同章节,他把自己在平型关、百团大战摸索出的规律代入,一旦感觉文字与实际战场动作脱节,立即返工。
高负荷工作导致左眼经常泛红,泪水止不住往下滴。警卫劝他戴墨镜,他摆摆手:“看得清楚要紧。”恰逢盛夏,大连昼长夜短,他却几乎把白昼黑夜都装进了条令里。星期日也不除外,偶尔海边散步,也是边走边想——某个术语换个措辞是否更顺畅?助手暗暗算了下,七周时间,刘伯承日均伏案十一小时,硬是把21万余字译稿逐行逐句校改一遍,外加6000多字“译本说明”,把苏联卫国战争经验与中国战例对应标注,方便部队学习。

有人不解:度假为何搞得比上班还累?在场的编辑笑言:“这就是他的休息方式。”站在纯功利角度,刘伯承此举省下的时间成本难以估算;从军事建设角度,这部条令为后续合成军、炮兵学院课程提供了现成教材,价值更难折算。不得不说,他用个人健康置换了全军的理论加速。

9月下旬,海风已带凉意。审定稿全部装订完毕,彼时的刘伯承体重大概掉了三四斤,却格外精神。助手打趣:“账是彻底清了。”他点头:“翻译账还完,还得接着学。”10月初,他带着厚厚成稿坐上返宁列车,窗外树影后退,海线渐远。没有告别仪式,没有大段感慨,下一阶段的教学计划已经在他的笔记本里排得满满当当。
长胜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